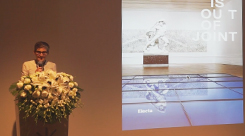藝術中國: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我們這一期的藝術沙龍節目。今天請到的嘉賓一位是藝術家、中央美術學院教授朝戈老師,一位是來自維基國際藝術品修復中心的邰武旗老師。邰老師最近組織了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中國油畫院舉辦的“中國精神”大展。我們從朝戈老師最近的維也納展覽開始聊起。幾個月前,朝戈老師的“瞬間與永恒”在維也納的藝術論壇博物館開幕。距離上一次朝老師在歐洲羅馬的展覽有九年的時間。朝老師您能來談談這次展覽的情況以及您對歐洲的人文環境的一個感受?
朝戈:簡單一點,維也納這個城市讓我們感到很興奮。德國基金會辦這樣一個展覽讓我感到很高興。這個美術館是奧地利國家銀行的美術館,也接納了20世紀西方很多藝術家,包括畢加索、馬蒂斯這些藝術家,能在這里辦展我還是感覺很好。我覺得維也納的觀眾還是很獨特的,跟羅馬的和巴黎的相比還是不完全一樣,他們會更認真一些,會對你的藝術產生很多疑問,這其實是很好的交流前提。
藝術中國:維也納當地也有很多收藏,包括博物館、很多知名的批評家,您這次在歐洲待了幾個月,在這一方面有什么新的感受嗎?
朝戈:我們這次過去見到了很多專家,有博物館館長、美術學院教授、藝術活動的組織者等等,幾乎都中年之上吧。雖然我們之間的交流并不是很長,但和這些專家交流的過程中我感受到兩個信息:一個就是,他們其中從事繪畫的人很少,絕大多數在搞后現代的藝術,波普多一些。所以我們在交流的時候他們也有很多疑問,特別的認為“你為什么堅持繪畫”。但是他們架上還是比較多的,搞裝置的也有,但多數還是架上。我在2013年的時候在巴黎做過一次展覽,這里和巴黎的觀眾相比還是不太一樣,和羅馬也不一樣。就我個人來看,他們的差別在于一個地域產生的藝術家的一個大的群落造成了那里的氛圍,比如說羅馬產生了文藝復興,古代時期產生的藝術家群落非常強大。巴黎也很強大。維也納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產生了分離派,這三家的產生卻是也難能可貴,但相比西歐還是要弱一些。
藝術中國:這次展覽主要展出了您近二十年來的代表性作品,還有一些風景畫和素描。您的風景和素描可能是我們以往比較少見到的,能談一下您關于展出這一部分的想法以及作品中您想表達什么?
朝戈:我覺得個展總體來說應該有較大的時間段,時間段就意味著至少得要十幾年的。你一年可能會畫很多,但這一年里的作品往往會有種共同的氣場。另外一年的,或者十年前的創作就會有另外一種氣場。盡管一年內的作品可以有很大的變化,但一年內的作品往往還是相似的。所以我的個展我還是希望能在時間上產生一定距離。題材的距離也是,比如原來我畫的風景比較多,現在也畫一些建筑,或者接近靜物的作品,這里頭也有一些探索。從這些作品我希望能讓觀眾看到我的思維也是逐漸發生變化的,比如藝術家是我一直熱衷的題材,但逐漸地你會發現新的題材、新的內容,你也在成長。這個無法避免,我不能總畫青年時候的那些題材,藝術還是有它的豐富性的,當你的語言相對來說比較熟悉、比較自如以后你的題材會擴大。
邰武旗:我想問一下,剛才說的最早的展覽是哪一年?你覺得這幾次展覽從觀眾層來說,從交流溝通這方面來說有多大的區別?
朝戈:最早的是羅馬的展覽是2006年,巴黎的展覽是2013年,今年是維也納。我覺得從性格來講,羅馬是最強烈的,在羅馬我接受到很多擁抱,美術還不像表演藝術那么煽情,但那里的觀眾非常熱情。他們不會問你“問什么這樣做?”,好像馬上就能明白你的藝術中他所喜歡的地方,甚至會認為這是他期待的藝術,這是羅馬。
藝術中國:我記得您在一篇文章里提到過觀眾的表現,他看到你的畫感覺“后背要燃燒起來”。
邰武旗:所以我一直覺得這種形式,這種觀展氛圍現在在我們這里反倒非常稀薄。應該說我們對作者和作品更了解,但相比之下卻不如那邊。出國辦展看起來是件新鮮事,但實際上從早先的到現在的有很多藝術家都出國辦展覽。但是出國辦展卻有本質上的區別,出國辦展挺容易,但是展覽所涉及的作品跟當地的人能夠產生共性的交流與共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我們辦展的根本目的應該在這里,我們不能說辦一個展覽就貼上一個標簽,要有“多少個”展覽,展覽不是履歷,作品能夠跟觀眾交流是最主要的。所以我有一次看到關于您(朝戈)的文字報道上面說您出國辦展覽,作品同當地觀眾之間的交流互動,那種共鳴是共性的。您曾經有過關于內蒙、蒙族的比較東方的題材,其實這都只是掛了個“牌”而已,這些風格、題材可能最終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找見這個共性,這個共性能夠讓大家得到一個共鳴。這幾次展覽我看到的相關報道都涉及到這一點。我們現在的展覽太頻繁了,幾乎每天都有開幕式,但真正能讓人記住的,或者說作品與觀眾產生交流的作品太少了,這一點在朝戈老師的作品中有非常直接的體現。包括在油畫院的展覽以及我們平時所看到的作品,外在的東西可能就退到后面去了。大家經常談的風格、樣式、形式這些東西,包括“民族”這些畫了“圈兒”的東西都開始消解,你能感受到的是那種凝重的東西,都在安靜之中,這種“安靜”是一個真正擁有批判精神的作品才會有的東西,這種姿態是一種批判精神,而不是張牙舞爪,也不是說那種直接的、外在的或者說夸張的東西。安安靜靜地站在那兒看所有的東西。就像這個題目一樣:“瞬間與永恒”。你就能感覺到我們眼前經過的瞬間都是永恒的,但留下的永恒是什么?真正的永恒就是從精神角度出發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不論是出國辦展還是在國內辦展,不論在哪里,作品本身呈現出來的東西是否能夠跟人的內在有所溝通。
藝術中國:每次朝戈老師出國辦展覽都會受到很多的關注,尤其是更才提到的06年的羅馬展覽,可能更多的在于您的作品中對人的關注。羅馬是發生了文藝復興的地方,他們對人的關注,對人的解放和尊重是不是同您的作品產生了碰撞?您這次在歐洲的時間里,關于歐洲的這種人文傳統您又是怎么看的?
朝戈:坦率的講,我對歐洲一直是很向往的。我們東方也有很多優點、很多的積累,但是歐洲一直給我更加現代的啟示。我們所說的“人文”,其實在中國也是豐碩的,但在歐洲的近代發展的非常的飽滿,包括藝術、包括社會結構等等有著非常豐富的實踐,這是有魅力的。我一直認為人類的生活是彼此學習的,彼此都是有弱點的,彼此學習能夠使自己的不足的以改進。其實人類和歷史的發展進程是有關的,所以我一直覺得歐洲是我所向往的,我們也能看到歐洲一些新的變化,這對我也有打擊,我一直認為歐洲在世界上是比較好的,他們曾經處理了各種各樣的人類問題,相對來說會好一些,這是我的看法。
邰武旗:回到藝術本身來講,那邊實際上就是我們的鏡子,特別是架上繪畫這一領域。現在在歐洲可能有很多的地方架上繪畫在往下落,我其實這幾次去倒是獲得了另外一種信號,好像倒不是這樣的,好像越來越往回返,好多比較大的博物館也開始把近幾十年以來的當代的作品當作標本保留,騰出一些位置來給現代者。我當時去了好幾個美術館,我發現這是很新的一個東西。最終我們藝術的標準到底是什么?“新”不是唯一標準,人類一步一步這樣走來,什么是“新”?在我們的見識里能看到的東西非常有限。什么是舊?其實我們也很難去見證。這些都不太要緊,要緊的是我們的品質是什么,我們的精神到底是什么?永恒的價值到底是什么?我們還必須去相信這些東西。不像現在說的資本啊、商業啊、娛樂那樣,把藝術這件事弄得快要失去對它原來的敬意了,就是藝術本身的敬意就快要失去了那樣,這個就我個人來講是非常不舒服的一件事。我們的生活都沒有時間概念,把一切變得有些荒誕甚至荒謬,非常快速地去運轉,那一切看在眼睛里,給心靈留的空間太小。但這個東西又不可能強求,但我看到西方很多美術館、博物館讓我感到很欣慰,大家可以安靜一會,一切事物絕不是以新為標準,一定是以品質為標準。包括架上繪畫,我們要談這個主義、那個流派、個人風格這些都是不要緊的東西,要緊的是甭管你是什么風格,你是不是做到了那個高度,你是不是有那個水準。現在大家都開始往回返這個東西,包括人文的,不僅僅是繪畫,還有電影,比如我們之前談到的《都靈之馬》(電影名稱),這個出現的時代非常晚,雖然是近幾年的事情,但是部很好的電影。也包括我們現在談到的娛樂性的東西,在“裹挾”著的這樣一個社會狀態里也有好的,也有非常值得承鑒的東西。像朝老師這種精神追求的東西,還有影視圈的、文學界的、音樂界的其實都有非常多的好的東西。現在大家開始冷靜一點了,幾十年的過程中大家開始有些辨識了,純粹的商業、純粹的資本、純粹的娛樂是不是還能夠滿足自己精神的需要?這種空間到底還有沒有?已經開始感覺到這種凄涼,這是好的現象。
藝術中國:我剛剛在國外待了兩個月,我覺得往往過去的媒體包括油畫界一開始就談中國和國外的區別,但現在好像大家越來越談到的是二者間共通的東西。一件藝術品不管是哪個流派哪個藝術家的作品,對于觀眾來說能否真正打動人心才是重要的,哪怕就獲得一個字“好”,就是好的作品。我們過去看西方的眼光好像要多于西方看我們的眼光,但現在真的是越來越相互的學習,我也想聽聽朝老師您的看法。
朝戈:西方有時候會把我們看成“他者”,這個也是有問題的。當時我在自己的展覽上發言時候談了一個問題,結尾我說“我希望使藝術回到良知,回到人類的共同的詩意”,這個有一個共同。我們現在看到的比較多的現象是藝術越來越陌生化了,越來越讓我們不熟悉,不光普通人,我們藝術家也不熟悉了。那么這里有一個問題是,20世紀以來,人們對自我的認識比較偏狹。藝術不是一個極端的自我表現的產物,我們需要一部分藝術家使藝術回到人類共同的理解力里,回到共同的詩意,這個詩意現在肯定是失去了。這是我今年一個比較重要的觀點,我們要往回走,往共同走。我對西方來說很陌生,但是藝術就是可以把我們這些非常遙遠的人們聯系在一起,然后大家都很激動,我們可以有一種溫暖,我們可以對人類的問題有共同的共識,或者差異。我還經歷過,觀眾有的時候會很激動,和我談了很多個人的東西,談自己的家庭、自己碰到的困難,他們說他們的心情和我非常相似。我們原本是陌生人,但為什么會這樣?這就是,藝術可以溝通人類的心靈,可以增強我們真實的理解力。藝術確實能夠使大家有心靈的交流,擺脫地域與種族的隔絕,通過藝術確實能夠讓大家共同面對問題,這個我是有例證的。我們雖然會共同面對一些問題,但西方也把我們當作“他者”,認為“你”是中國人。包括這次展覽,也有人說到,你們中國的藝術90年代的時候怎么怎么樣,80年代怎么樣,你的又是怎么樣,會把你推的很遠。我們不用對他們把我們當作“他者”感到奇怪。但更需要我們去突破這個點。
邰武旗:您剛才說的很對,我們不用去感到奇怪。這么多年來,我們一直是“東方”、“西方”不管別人怎么說,我們自己首先這么說,包括“先進的文化”、“落后的文化”,我們總需要要這樣去判斷自己,不管別人怎樣判斷,實際上久而久之別人也會這樣來判斷我們。但藝術就是讓我們變得寬大,文化本身就是讓我們變得寬廣起來,不要那么狹隘。這里包括我們中國人非常功利的去想的問題:藝術該怎么做?該怎么去操作?這完全已經不是藝術本質上的東西了,而是完全外在的研究性、學術性的東西了,這可以成為另外一門學問。您剛才說的“不用奇怪”,這個心態非常正常。當有一天我們都覺得朝戈老師在那邊(歐洲)辦展不奇怪,那邊的作者來我們這里辦展也不奇怪時,我們就等于直接把中間隔著的障礙全剌掉了,這時候就是人跟作品在產生關系,這樣就正常了,這是人跟藝術在開始產生作用,人跟藝術之間有聯系了,現在我們中間設置的東西太多。
藝術中國:這也是我們所說的文化交流的目的,現在往往很多藝術交流被強加地賦予了很多意義, 其實這就是對彼此生活方式或者精神世界的一種交流完成么剛剛朝戈老師也提到了西方20世紀以后的現當代藝術對于中國油畫的影響,我覺得我們對于西方現當代藝術影響的態度轉變也是在短短的20、30年之內變化的,80年代我們還接觸不到更多的信息,一開始主流文化的排斥到今天我們可以自由的去欣賞這種轉變也是在短短的30年之內完成的,對此朝老師您怎么看?
朝戈:我們從一個大的維度來看這幾個世紀、甚至幾十個世紀,20世紀是非常特殊的,西方從19世紀末就孕育了一種不安,一種蛻變。20世紀初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實際上20世紀是具有摧毀性的,它開了個頭,在西方發生了他們并沒有預料到的、非常強烈的粉碎性事件。戰爭帶來了巨大的破壞力,這個破壞的結果實際上就是把啟蒙主義(運動)或者文藝復興以來的樂觀主義徹底打破了,隨后才出現了荒誕。但是我們現在怎么看20世紀?20世紀形成了西方藝術的新標準,我個人覺得20世紀是比較令人質疑的時代,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懷疑主義、虛無主義或者人類的健康理性被粉碎以后呈現出來的狀態。我們大家都聽過搖滾,很多人聽不慣,這里面有很強的男子漢嘶啞的聲音,實際上我覺得那是精神崩潰以后的精神現實、情感現實。對于20世紀的主導精神來說我是持批評態度的,它是非常頹唐的。西方也有很多學者同我的看法一致。 面對這樣的問題,我覺得我們要重視我們這片土地上產生的渴望,我的藝術里有很多20世紀不怎么流行的抒情性、詩史性或是沖突感,這是我們的精神,我們不要以對方的藝術標準來誆我們自己,把自己給裝進去,如果這樣那么中國藝術的前景就不會好了,我們對社會現實以及未來會有新的渴望,也可能有新的悲劇感,但我們東方藝術家應該有點獨立性,不要完全服從他的標準。當然,有意義的部分就是20世紀西方做了很多“實驗”,這種實驗精神給我們提供了很多在第二層次上值得吸收的東西,實驗是有價值的,我們要揚棄一些東西,我對20世紀也有一些審視,有很多東西還是可以吸收。
邰武旗:延續國內幾十年以來,從80年代到現在,我們對看到的東西都有點食古不化。比如對于反權威、反傳統似乎是能夠體會到,但是我們對新生活包括商業社會真正的反思還不太習慣,這樣就造成現在很多問題。20世紀藝術到我們這兒以后,我們做到的和沒做到的好像給我帶來這么一個感受:有非常多的反思我們并沒有進行,特別是怎么面對商業社會的問題,藝術家以文化界的概念應當怎么面對的問題。我們的經濟、科技都在跟進或是改良,大家好像更愿意去接受反傳統、反權威,這可能跟過去的慣性心態有關系。我們非常容易地去反權威,但是反了權威之后留下的這個世界給我們的新的東西我們好像就不太習慣去反思,這樣就會逐漸積累很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