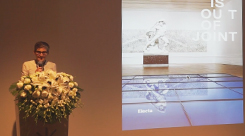出走,不僅是身體的遠足,更是精神的遠行和尋找。藝術家石煜和劉商英以“出走”為題的聯展正在798橋藝術中心展出,他們一位遠赴印度和美國66號洲際公路,一位遠赴西藏,因這些陌生景色與心靈的碰撞,創作出令人心旌搖動的畫作。在創作中“出走”還有另一層含義:對語言習慣的挑戰和觀念的實驗。
藝術中國:我們今天談論的主題是關于石煜、劉商英兩位藝術家在798橋藝術中心舉行的聯展《出走》。本次展覽策展人是袁佐老師,兩位藝術家都先后在袁佐先生主持的中間美術館做過關于寫生的大型個展。這次的展覽和之前相比有哪些不同?
石煜:我是2013年3月初的時候在中間美術館做了一個名為《各色》的展覽,是由彭鋒老師擔任策展人。展出的作品是我在印度和北京畫的部分夜景,強調繪畫語言中的色彩特點。策展人在起題目的時候考慮得比較多,希望能夠把我的出身,就是父輩曾參與過無名畫會的經歷,我在美院受教育的背景以及我的作品整體貫穿起來,那個展覽是比較完整的一次個展。
做完中間美術館的展覽后,我開始把自己的作品和展覽的主題一起壓縮,我和劉商英兩個人一直也在不停地溝通交流。其實我們倆2006年在美院的地下展廳做過一次聯展,也是我們出去畫了一批畫回來以后做的一個展覽,有點類似教學匯報展的性質。這次在798的展覽會有老作品。也有新作品,老作品是前幾年在印度寫生時的一些積累,新作品是今年夏天我跑到美國66號公路去畫的一批畫。主要的想法是把《各色》引出來的主題繼續深入,打開思路。展出的作品包括在印度畫的寫生、美國66號公路以及最新創作的城市夜景,這三種題材是穿插在一起的。
劉商英:8年前我們一起做展覽的時候,身份剛從學生轉變成老師,對繪畫的認識,對生活的認識都還處于探索的階段。我倆師出同門,上學的時候都在油畫系的二工作室,工作室的主張是追求繪畫過程中的“短兵相接”,在寫生當中強調直覺,強調色彩,畫面中的張力……這些內容都給了我們很深的影響,在腦子里扎了很深的根。之后慢慢隨著對藝術思考的深入,各自經歷不同的道路,時隔多年又有機會一起做展覽,并不是故意為了延續8年前的展覽,而是正好有這樣的契機。這就是我們在彼此的探索道路上找到了共通的東西,我覺得這共通的地方來源于中國整個大的繪畫環境,也來自我們共同的學院背景,我們有過一些共同的經歷。
在繪畫當中,我們共同堅守的一個理想就是通過繪畫最原初的直覺狀態去傳導出我們在生活和繪畫語言形式上的感受。我們找到的共同出口是寫生,寫生所涵蓋的面很廣、很大,他去了印度、美國,我這些年都在西藏。我們“出走”,出去畫畫不在乎畫的大小、材料的種類,“出走”更有意味的是像中國傳統畫家或是西方印象派以來的畫家那樣,離開畫室,來到戶外,它強調的就是直接的、沒有過多理性束縛的繪畫過程。我們對此一直都有非常大的熱情。
藝術中國: “出走”這個詞含義第一是地理空間上的概念,走到異域,到一個陌生的環境去寫生,另一方面,其實是有一些遠方的的東西吸引著自己,是一個不斷開拓和發展自己的過程,兩位怎么理解?
石煜:我們經常被“習慣”所干擾,看問題的方式和解決問題的方式都是約定俗成的,這個在藝術創作中其實是阻礙藝術發展的。怎么樣才能打開一扇門重新看待問題?我覺得“出走”就是帶有這種含義——離開習慣。8年前我們一起做展覽,那時候我們想的主題也是不要束縛在習慣里。有時候人的發展規律是我們各自走著自己的路向前時,沒準在某個路口就相遇了,殊途可以同歸也可以不同歸,相遇的時候又會遇到新的問題,我們都帶著這樣的問題再重新做,這是在藝術發展過程中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袁佐老師提的“出走”說的是離開,就是人離開和心打開,人需要離開習慣性,才能打開心性。
劉商英:“出走”除了習慣之外,還有尋找的意思。尋找的不單單是具體的物象,而是作為一個個體尋找與更廣闊的天地之間的聯系。這種聯系會幫助關照自己,使自己不至于局限在一個很小的環境里面。
藝術中國:石煜老師這次展出有兩個地域的寫生作品,一個是印度,一個是美國66號公路,這兩個地方給您帶來了什么不一樣的感覺嗎?
石煜:去印度是一次偶然,我和劉老師一起去的,是美院的活動,大概有30多人。印度完全是一個陌生的地方,我也不知道那里會有什么有意思的,但是我對宗教、佛教的東西挺感興趣的,就隨身帶了一個本。但是到那里之后3、4天什么也沒畫,沒進入狀態,不知道要畫什么。后來有一天晚上我們要去酒吧,租了當地的一輛車,結果無意中就深入到了當地的巷子里面去了,就在那一天,我突然發現那里面有許多有意味的東西,和畫有關系的東西。
劉商英:就是離開了旅游景點,真正進入老百姓生活的地方,那種鮮活的感覺一下子就進來了、打通了。
石煜:特別有意思,給我的感覺就是“接地氣”了,一下子找到了畫畫的根源了。我后來畫了很多關于瓦拉納西恒河的畫,恒河是印度人的母親河,是一條古河,就像我們的黃河一樣,守護著他們的文明。在現場,我能夠感受到文明古國的“古”以及古老文化和現代文化的關系,那種氣息撲面而來,這些非常吸引我,于是就決定畫一批這樣的畫。他們的那里色彩,非常濃郁,而且有氣味感,除了視覺感外還有嗅覺感,這是我從當時的現場體會到的,我特別想把這種味道感畫出來,帶有咖喱的味道。除此之外,色彩中還帶有宗教的神性的感覺。
劉商英:這就是每個人的性格不一樣。他在印度找到了和他個體關照、他平時所想的一致的東西。這些東西能夠把他內心的一些想法感受帶出來,然后直接的反映在了作品上。
石煜:入必有得。所以出走一定有收獲。去一個不熟悉的地方,剛開始也會有迷茫、徘徊,但慢慢的就會發現一些新東西。在中間美術館做展覽以后,就想把這個主題展開來,于是開始尋找相應的契機。我跟一個朋友聊天,他提到了“公路寫生”,我看了一些有關公路題材的電影,里面就提到了美國66號公路。就像塞林格寫的《麥田的守望者》,他也是穿越了這個公路,還有貓王,他們在現實中同樣比較迷惑,于是就離開自己習慣性的生活,駕上一輛車,沿途走,遇上一些人一些事。這里面帶有故事性,人在尋找故事,想要離開現在的生活,顛覆一下,換一個活法,換一個生存方式。當時跟朋友聊的時候說到66號公路挺神的,我就想試一下,后來就找了一個契機,安排了大概一個月的時間,帶著朋友、家人,沿著他們當年的老路邊走邊畫,那路的全長大概3000多英里,從芝加哥到洛杉磯。
劉商英:他選這個路很有意思。路是溝通人與人之間重要的工具,是文明發展很重要的組成部分。
石煜:美國66號公路是美國精神的一個縮影。因為當年這是一個很發達的地方,我們現在熟悉的汽車旅館、加油站等,最早都是在那里興起的,是現代化生活的開始。美國是輪子上的國家,他們比較有意識的將這個拓展開來形成輪子上的文化,就是行走、穿越這樣的一個文化。
藝術中國:這一個月的時間里,遇上的比較感興趣的題材是什么?
石煜:還挺多的。被警察逮到后查身份證、駕駛證,我們在北京這邊養成的開車習慣跟美國那邊是不一樣的,他們很講秩序。他們把公路變成了一個公路博物館,那條公路已經荒廢不用了,也不會去修它,就讓它自然的在那里。一路上留了很多的遺跡,那些遺跡讓我很感興趣,有些廢棄的汽車,插在地上,來往的人可以任意往上面噴漆,于是那就成了公共藝術,這些廢棄的汽車就變成了大家對這個東西的紀念,路過這里,大家都可以去噴繪一下。很多人會對曾經發生過的事情,行走過的路有一個懷念。
藝術中國:印度的特點是古文明和宗教,而美國的66號公路則是現代文明的興衰,您對似乎這兩方面都很關注,從而引起了興趣。
石煜:對。我自己畫寫實,就很喜歡兩級的跳躍。它們之間的沖突挺大的。我是借助它們來表現了自己。
藝術中國:劉商英老師選擇了西藏,是不是覺得那個地方更原始,和自然更相通?
劉商英:我和石老師的路徑不一樣。這個路徑代表了我個人的態度,我更愿意去一些沒有人或者人少的地方,這倒不是因為我要去隱居或者擺出一種姿態,而是在那種環境中我可以找到自己是什么。因為每天在城市里面忙碌,都是應接不暇的。作為一個藝術家,要保持一個清醒,知道自己的選擇是什么,反映在作品中的脈絡要清晰。
這次的展覽恰好從題材還有方式上碰上了,其實我在四年前就開始思考這樣的問題并且開始做了,每年都會去一個地方,我不知道這叫不叫出走,就是去尋找一些冥冥之中感受到的東西,或是一些困惑,如果積極的去對待這些困惑的話,它會是藝術的一種原動力。我們不約而同的選擇這樣的方式,它是符合我們內心的。
藝術中國:我們很想知道您在西藏的工作狀態怎么樣?在海拔那么高的地方,很多時候可能會出現缺氧的狀態,在那種條件下是怎樣創作的?
劉商英:可能大家都關心這個問題。我去之前也擔心這個問題,但后來發現這些都不是問題。雖然西藏和平原有很多不一樣,但到了那里自然而然就適應了,就開始工作了。我要去那么遠的地方工作,是因為有動力驅使自己到那里去,在這樣的動力下會讓我覺得沒有什么是大問題。
石煜:其實只要有了目的,有了自己的動力,好多問題都不再是問題了。畫畫的時候總覺得會遇上許多生活上的阻礙,這其實就是因為沒有拿出足夠的勇氣來。做很多事時是需要勇氣的。就像劉老師去西藏這件事,很多人不是去不了,而是心里想的和要做的事的動力沒有大于一切。這是藝術探索里面很可貴的地方,不是要把事情做得完完整整,漂漂亮亮,端在別人面前,藝術最感人的是偶然間發生的,自己都不知道會遇見什么,會發生什么,這是最吸引人的。
藝術中國:您這次展出的作品有些是寫生的,有些是在畫室根據記憶沉淀創作的作品,這兩種狀態在您身上是不是不可分割的?
劉商英:是的。首先我沒有一直在外邊畫寫生的條件,總要回來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回來的之后比在現場難度更大,難度在于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環境當中,要面對熟悉的工作和生活,同時經歷過一些事情之后不是要憑借記憶感覺去作畫,而是靠著一種感受之后的沉淀,所以在工作室里畫畫的遍數要比在現場的遍數要多,它需要反復,這種反復和現場寫生是一種很重要的互補。畫畫不只是一時的沖動和興趣,而是要像拉斯科洞窟壁畫一樣,到今天還能給人心驚動魄的恒久感覺。這兩種不同的工作方式可以幫助我不斷的去矯正這種關系。
石煜:我們都是搞架上繪畫的。在媒體傳播方式很多元化的今天,我們還選擇一種很傳統的用手在紙上、畫布上涂抹的方式。這是個人的選擇,我就是喜歡有觸感的東西,我覺得筆在紙上運動的感覺就像是心電圖似的,這種運動感永遠帶有自己心性的東西,很難被代替,心情躁動時候的運筆和心情愉悅時候的運筆肯定不一樣,這種不一樣是人的味道,代表人最原始、最初衷的感覺。
藝術中國:以前我們說寫生都是為創作打草稿、積累素材,那現在兩位老師是否覺得寫生和創作是一回事,“出走”這種寫生方式在未來會是你們重要的創作方式嗎?
劉商英:不一定。首先寫生和創作沒有明確的界限,都是繪畫。然后,我不能說我以后就一定會是這樣,沒有最終的定論,這是沒有預設的。咱們剛才談的問題,我突然就想我這次展覽就不展出寫生的作品了,全部展出我在工作室創作的作品,這實際上是我腦子的“出走”,回來之后在工作室完善的過程,這里面不存在是不是一定要出去寫生。就像我很喜歡的一個電影《阿甘正傳》,他用跑步的方式演繹了他的一生,他想起來跑步就跑步,等他跑出名了,一大堆人跟著他跑的時候,他就不跑了,沒有理由,就是跑累了,該回家了。其實藝術也就是這樣,它是一個自然生長的過程,我們倆選擇不同的方向出走,是我們倆此時此刻某些狀態的共鳴之處,但誰也不知道今后的藝術之路是怎樣的,不能提前設定這條路。我很熱愛繪畫,我一直在想,繪畫不是一個形式的問題,也不是語言的問題,而是通過繪畫表達自己的態度,和周圍的關系。這里面的狀況是自由的,不可預定的。
石煜:寫生只是一個方式而已,它的起點應該是自由,我的理解是從自由到自然再到自由。先是因為心性上的自由出去了,藝術上的手法自然的生長、發展,最后回歸的還是自由。
藝術中國:兩位老師剛才提到“出走”不僅是身體上的離開,更多的是意識方面的,從意識方面來講,你們想要離開和尋找的是什么?
石煜:劉老師剛才有提到西藏。他心里是有一個標準的,但這個標準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他要去找的也是這樣的標準,當這兩個標準相遇的時候會發生碰撞,那個時候的畫呈現出來的感覺是不一樣的。我也是這樣。我想象中的66號公路和我真的到那之后是不一樣的,就是短兵相接,見招拆招的感覺,那種相遇是無法設定的。這就是藝術的偶然性,偶然性里也含蓋著某種必然性,是一個偶然性的發生,但自己對這個偶然性有一個相應的計劃,偶然和必然相互穿插。
劉商英:寫生受客觀原因的限定,不允許有太多反復的過程,所以在現場我會給自己限定一個時間,不管畫得是好還是不好在規定時間內一定要完成。在工作室就不一樣,一張畫,我可以很快畫完,同時也可以不停反復的畫,這兩種感覺是最不一樣的,它像是桌子的兩面,雖然不同,但都在桌子上,這兩種方式是相互補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