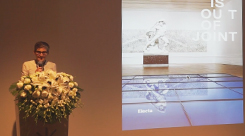梁克剛:各位觀眾朋友好,今天我們非常榮幸來到了藝術中國的錄播現場,我們是參加這個藝術沙龍,正好邀請了藝術家邵譯農先生和張帆先生,剛好他們也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無常之常”展覽的參展藝術家。今天我們也把他們兩位請到這里來進行一個現場的交流,因為我們這個展覽剛剛在第四站的歐洲巡展,德國的彼得爾多夫北方藝術節,這是德國最大的一個藝術節,在那里得了一個大獎,我們這個展覽被好幾萬個觀眾投票評選的,今年度的北方藝術節的展覽的大獎,這是一個非常歡欣鼓舞的消息,今天我們也就這個話題深入交流一下。這次展覽已經從去年的威尼斯雙年展開始,之后到了波羅尼亞,然后到了德國的波恩,第四站呢是到德國北方藝術節,獲得了這樣一個獎項,所以呢,我作為一個策展人也有感慨,今天約兩位來深入地聊一聊這個事情。因為這個展覽獲獎的消息剛剛知道,北方藝術節規模非常大,每年有大約兩百五十位藝術家參加,這一站你們沒有去現場,那么我給你們介紹一下,今年這個北方藝術節一共有50個國家的250余位藝術家參加展覽,有幾個大的展廳,一個是咱們“無常之常”展廳,俄羅斯還有一個單獨的展廳,按說主賓國應該是俄羅斯,但是我們得了一個大獎,在開幕上效果非常好,這個展覽受到了特別多的關注和觀眾歡迎,上個月我們接到通知,整個北方藝術節展期是四個月,數萬個觀眾投票,最后毫無爭議的,我們的展覽獲得了今年的大獎,這也反映了我們展覽的學術理念、美學訴求在歐洲得到了非常大的認可,我想今天借這個機會跟你們兩位參展藝術家做一個這方面的交流,老邵你談一下你的看法。
邵譯農:當時蕭蕭、老郭他們拍回來照片,看到現場就非常激動,這次展覽的布置,整個從空間到現場的感覺,充分地把無常之常的理念表達出來了,而且每個作品之間的關系,空間的感覺,其實非常具有連貫性,而且有中國人移步換景的美學特質在里頭,聽說現場專門有保安把門,觀眾要參觀后來就要排隊,作為一個參展藝術家我確實很受鼓舞。
梁克剛:我先介紹一下這個展覽的情況,這一站確實是四站歐洲巡展里面展示效果最好的,北方藝術節的組委會特別給力,他們完全按照我們預先做的展場設計,做了一個展覽背景現場,現場的設計我們當時提了一個理念,就是借用古典園林的造景的方式,那么中國古典園林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設計理念,實際上它用借景生情和借物抒情,它不是一個單純的自然景觀,利用了心理感受和自然的景觀之間產生對應,形成一種很有意思的帶有文化氣質的氣場,影響在景觀中的人的感受,所以我們這個展覽的設計有一種突破,跟一般性的西方展覽不太一樣,我們把環境作為了展覽的一部分,這次的組委會特別支持,聽了之后非常激動,決定完全按照我們的圖紙來進行,布展的時候讓環境最大限度的放大作品的特質,包括建構作品與作品之間的關系,甚至說把觀賞路線,看的過程中產生的體驗也作為一個展覽的要素去考慮,所以這也是這次很多觀眾來了之后特別興奮,感受特別強烈,容易去體會中國東方的美學的一種場域的概念,這次我們也很開心碰到這樣的一個組織方,這個組織方的總監是藝術家出身,所以他很能理解藝術家按照他們的方式布展,愿意最大限度地給予工作上的便利甚至資金和現場布置方面的支持,所以這一站在展示效果上有很好的特點,我們之前在展覽的理念上有很多的交流,這個展覽從籌備到現在為止接近三年了,包括怎么去通過這樣一個展覽,讓西方看到中國傳統文化里的精神和美學特質,這個老邵應該有比較多的體會,因為老邵最近十幾年的工作重點也有很大的轉向,老邵談一下創作上的跟展覽之間的關聯。
邵譯農:我覺得中國藝術里頭有講氣和場,講場力,這個力量能不能夠波及到整個空間和場里頭,其實作品的氣息和整個的氣韻氣勢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在一個場里頭物品和作品之間形成的場力是一種非常有直覺感的東西,這種直覺抵達到這種地方的時候,能夠把場的空間的使用在自己的氣的控制的范圍里頭,這個時候場就產生了一種非常特殊的直覺的力量,這個時候的氣你是控制的住的,德國的展覽本身氣質之間的特點和場地的控制是非常有意思的,跟過去的純粹的白盒子之間還是有非常不同的地方。
梁克剛:張帆的創作,最早看了你的作品,覺得是非常國際化的,跟西方整個抽象的系統是非常接近的,但是我看到你最近幾年的作品,也邀請參加這個無常展,你最近幾年的作品有非常大的變化,代表了很多中國藝術家最新的一種趨勢,原來從非常關注國際當代藝術包括西方視覺藝術的方式,到循序漸進地有意識的跟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視覺藝術去接軌,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所以我想你也可以根據你的作品和展覽之間的關系簡單說幾句。
張帆:我先說一下剛才你說的展覽場地的感覺,雖然我沒去,但是我從現場的照片來看,比如說你說到中國園林,我印象中在威尼斯的場地是比較狹窄的,中國園林講究一曲三折和半遮半掩的感覺,哪個空間我看照片的時候是有這種感覺的,比如說中國園林不像歐洲園林,它有特別蜿蜒的這種感覺,所以這個展覽最后好也好,不好也好,策展的理念和參加的作品能融合到一塊,真的不在乎場地條件怎么樣,如果所有人看到都會感受到這個意圖特別清楚的話,無論大空間,小空間,所有的場地都可以做到很清楚地傳達給觀眾。關于我個人的創作,兩年多以前我個展的時候,我形容一下我跟中國傳統藝術的關系或者是如何碰到一起,我覺得是一個半推半就的關系,現在想這個說法也是比較準確的。在畫的過程中,當你進行到某一個結點或者階段的時候,你忽然發現你認識到的問題感到比較虛無的時候,傳統的無論筆墨也好還是章法也好,實際上能讓你有一個依靠的點,比如說我原來比較國際化的東西,那個就是我畫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忽然覺得我到底要畫什么,畫畫這件事你是在干什么,其實這個問題就在中國的書法、文人畫或者中國的筆墨里頭,所有西方不管是表現主義還是抽象表現主義,幾乎每個人都會受到這個影響,無論承認還是不承認,至少從他們的作品里面我是看到這個路徑在滲透到他們的畫里面。
梁克剛:我對這個感受很深,其實我以前是特別關注國際最前沿的樣式,當然國內的藝術家也能夠做到這個程度,但是慢慢隨著經驗和經歷的增多,我最后突然有這樣一種意識,世界上不存在一種純粹的個人,就是說你可以孤立于你的母語和本民族文化以及歷史傳統,脫離出來的藝術家是不存在的,包括看歐洲的特別牛的藝術家,其實你在他們的作品里面能夠看到基督教的傳統、古羅馬的傳統,包括古希臘的理性的、科學的和民主的傳統,最終的表現是非常當代和當下的樣式。所以當時看到你的作品感到很震動,兩年前在元典美術館給你做個展時看到你的作品我就感到很震動,我意識到你找到了一個通道,這個通道把你以往所受到了抽象藝術的訓練和傳統的文化和中國語境和你自己的血脈里的東西突然找到了一種結合點,這個結合點讓你的作品有了一個新的突破,這種突破就是說這種中國美學的氣質在作品中呈現出來,但是它的表達的樣式又是當代的和非常國際化的,是很容易跟國際的抽象藝術去對話的一種方法,其實我們這個展覽中大部分藝術家是這樣一個狀態,因為我們的定位仍然是一個當代藝術展,肯定不是一個復古的展覽,不是一個只是表達古代文化的展覽,就是想讓今天的藝術家從傳統文化中找到一種靈性的精髓的看不見的東西,然后最現代的東西中轉化出來,這是一種最當代的作品樣式,有傳統的文脈和文化的特質在里面。我想這也是這個展覽吸引西方的一個方面,我認為中國整個藝術上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就是我們現在復雜的現實,高速經濟增長,整個政治制度的不一樣,文化的發展所造就的豐富局面,各種社會問題,綜合在一起出現了一種非常有活力的和復雜的現場,這個我認為是中國藝術的很大的可能性和工作的領域;還有一個是我們有幾千年的與西方世界和其他地區完全不一樣的系統,但是我認為這個系統在休眠,在鴉片戰爭之后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失敗了,這個系統實際上是休眠了,在短時間內差不多兩百年內喪失了自信,但是這恰恰是我們在其中可以產生新東西的領域。這也是我當初跟老邵談論展覽的理念的時候想到的一個大的文化出發點,而且我想,在差不多三年前就開始討論這個展覽,就是想找到一個通道,在今天中國的藝術家能夠找到一個什么樣的新的機會向世界提供一個新的樣式和新的不一樣的當代藝術,我想老邵可以結合你的創作來深入地談這個話題。
邵譯農:我是覺得,我們經過將近一百年的向西方學習的路程,在這個路程當中幾乎是全盤接受了西方的價值觀,然后這三十年出現了中國的當代藝術,前面雖然有中國兩個字在這個地方作為一個地域的前綴,但實際上當代藝術仍然是學習來的一個東西,可以說這個版本我們從歐美一直借鑒過來的東西,它跟我們中國的古代的傳統走的完全是兩個非常不同的路,就像極一樣,一個是南極,一個是北極,在這兩個極之間,我們作為今天的這種文明,我們能做什么,我們不可能做古代的東西,也不可能完全是歐美的東西,我們自己還是要有對當代的感知和認識,其實應該是有一個今天的版本,那么這樣一個版本實際上走的是一條東西方文化的交融的路線,我覺得把自己今天對于傳統和西方的認識,這樣綜合的認識形成一個綜合的路數,在這個里頭體現當代人的個人的感覺和當代熱的文化的特點和價值觀,這個才是我們這個展覽最突出的地方和未來可能能夠成功的地方,我覺得這個地方的可能性比其他兩個地方對我們來說意義是比較大的。
梁克剛:當時在開始構想這個展覽的時候,我們也討論很多,包括展覽的題目,為什么叫“無常之常”。當時我們邀請了夏可君先生,就是人大的哲學教授,他也是在西方也學過西方的哲學,回來也研究過東方的哲學,最早呢我們也是想從東方系統和西方系統自檢找到這種哲學上的差異,當時大家的交流也比較深入,后來我就覺得整個東方的價值系統,我說的東方是指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文明,東亞文明的整個哲學和以地中海文明為中心的西方文明之間最大的差異就是對世界的看法,中國人認為世界是變化莫測的,是不可能去把控,人就應該去順應這個變化,而不是強力去改變它,我認為西方的哲學系統中人是比較重要的,把人看得很重,人是有能力代表上帝去創造世界的,這樣一個差異最后導致了文化、藝術、政治甚至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產生不同的應對方式,所以后來這個名字定為“無常之常”,所謂“無常”就是指世界變化無常,這個在中國的道教和印度的佛教里面都有類似的詞匯,后來我們找到了這樣一個詞,這種應對是什么呢?所謂后面的“之常”,我們想表達的就是,作為一個文化人和藝術家,在面對一個無法把控的世界的時候,我們如何去積極應對,而不是非常主觀和勉強地改變它。大家在創作的時候,帶有這樣一個出發點,所以這個展覽就這樣一路走過來,這個展覽的英文名字就是面對無常的意思。這個展覽在國外跟大家交流的時候也非常有意思,他們特別感興趣,認為這個展覽找到了這樣一個差異,找到了一種根上的差別。所以我認為就是說,四站在海外的巡展產生了一種效應,海外專業的藝術人士,大的美術館館長和重要的批評家到了我們這個現場之后,反應非常強烈,突然意識到有另外一個系統是和他們非常不一樣的。但是這些作品都是看得懂的,都是當代藝術,都是很容易被把握,都是按照現在的知識和對藝術的判斷很容易進入的,但是進入之后背后的這個核心理念是他們所不了解和陌生的,是他能夠感受到時非常高級的,所以他就產生一種渴望,他特別想了解,特別想問你,特別想跟你說。我認為以往出國做展覽的時候,他們都是居高臨下的,認為你是來學我,我是老師,你是學生,你是來向我交作業的。他很傲慢,他不屑于跟我們深入去交流,他覺得這種東西我們都有過了,你不過是換一種方式來又做一遍,或者帶著你們國家的文化的符號簡單地重新包裝了與喜愛,核心的東西在他那里,源代碼在他那里,它可以不斷地升級版本,但是我們只能去抄襲,這次展覽我覺得就是很有意思,我覺得讓他們降低了身段,讓最尖端的藝術界人士降低了身段,虛心地想問我們這個展覽表達了什么。而且我們也用了很多中國的方式,包括剛才張帆談到的,布展的方式,我們這個布展的方式是一個很大的革新,完全不是按照西方的當代展覽的方式來做的,我們按照中國古典園林的很多思想來做,當然一開始你說的很對,威尼斯就開始實驗了,但實際上是被迫的 ,當時的展覽條件逼迫我們這么做的,當時的威尼斯展場是一個貴族官邸,就是威尼斯很有名的貴族官邸,專門用雙年展做的,這個建筑是個幾百年的文物,墻上是壁畫,很繁瑣的巴洛克風格的古代的壁畫,墻上不準訂釘子,天花上不準吊東西,我們的作品完全沒有辦法展,就是我想掛一張畫都做不到,后來根據這個現場回來設計了一套展板系統,但是這個展板系統又不能太笨,所以我把它設計成了一套園林樣式的展板系統,感覺到這個系統是故意做的,是為這個展覽設計的,其實中國園林就是這個特點,因為中國園林最發達的地區就是在蘇杭,蘇州當年是人口密度非常大的城市,那些園子都是很緊地擠在一起,在方寸之間營造出一種模仿自然或者提煉自然的人文環境,所以蘇州園林的設計是很巧妙的,它充分地利用空間和視覺的遮擋和轉折的關系,制造出來不同的小場景,讓文人在里面產生感受,產生一些悲天憫人的情懷。其實這跟西方不一樣,西方的園林顯示一種改造自然的能力,把樹修成圓的,把灌木修成方的,擺成圖案,這個我認為為什么呢,其實根上還是世界觀的問題,就是西方人認為他們永遠可以改造自然,他們表達的價值就是改造自然的價值。
邵譯農:中國人理念是要跟自然融為一體,然后置身于自然這個環境里,對于整個人身心的一種愉悅程度。
梁克剛:我們還不是很簡單地順應自然,比方說中國人造園或者做盆景,實際上是經歷了美學提煉,其實樹是不會長成那樣的,中國文人有一種審美趣味,主觀地嫁接在這上面,其實他造了一棵自然里不會長成的樹。
張帆:中國古典園林的度是掌握地比較到火候的,不是特別的矯揉造作和過于精致,但是日本的園林和樹修的有點過分,每一根樹枝應該怎么長,都是設計出來的,這個就是關鍵在于把握。
梁克剛:中國文人吧,包括造園是中國審美的勞作的方式,剛才張帆講的度的概念,一定不會過,一定是點到為止,一定要留有空白,日本它缺少文人系統,它最后在文人系統之下有一個匠人系統,日本的匠人愿意把活干到頭,跟文人的方式還是有差別的,所以這次我們談的東方經驗和當代藝術,這個東方指的是東亞中日韓,并不包括像印度這些地方。
張帆:我覺得東亞藝術或者東方藝術跟西方是兩個時空里發生的事情,在過去的傳統概念和古典概念里面,最后一定會殊途同歸到一個方向上,現在當你把兩個時空對接起來,融合到一塊的時候,道理就是這些道理,規律就是這些規律,邏輯就是這些邏輯,最后殊途同歸到一個點上,所以這個展覽其實就是往這個點上在交流。
梁克剛:實際上我們這個展覽剛開始并沒有完全想明白,只是一種朦朧的意識,或者一種沖動,實際上很多事情是在過程中逐漸想清楚的,甚至說現在我們還有很多問題沒有想清楚。在后面的幾站中,把這個問題更加深入地去解決,我覺得這個展覽其實可以承載很大的功能和命題,只是說我們現在還沒有走到那一步,實際上它能傳遞這樣一種理念,而且讓西方充分感興趣,產生好奇然后來研究,其實我們已經做到了這些,波恩那一站是三月份做的。波恩那個地區,北萊茵地區有7個美術館,在2015年要做一個中國當代藝術的群展,有7個美術館同時在做,他們現在來的七八家美術館的館長和大的策展人,有很多作品都是按照我們這個理念在調,他們到中國來訪問的藝術家,開始去了解,甚至說開始挑選我們這個展覽的藝術家去參加,其實我們在文化上已經在影響他們了,我們已經在告訴他們,我們已經有一種新的樣式是與他們不同的,就是說中國的藝術家也可以做出跟他們不一樣的當代藝術,這是他們感興趣的,我認為這個效應已經逐漸在開始展開,我看到的受我們這個展覽影響的展覽至少有六七個了,多多少少都是往我們這個方向上靠,而且有很多藝術家開始意識到在今天應該更認真的研究傳統,從里面尋找一些文化資源來完成當代的轉換,我覺得這個展覽已經開始產生作用了。
邵譯農:我是覺得中國文人的心態其實是非常有意思的,他有一種生命體驗,這種生命體驗直接跟內心世界是有關系的,比如書他欣賞的一棵松,這棵松肯定不是挺拔的非常直的,在巖石上,在土壤啊,干燥程度非常嚴酷的底下,這個松長得非常費勁,這個松承受的壓力,其實是跟生命的歷程是非常有關的,因為中國社會是非常扭曲的,在這種底下,跟松的精神是非常吻合的,九曲十八彎,不是那種直接的做事方式,能找到生命的同感和對應。假山石,一塊完整的石頭被時間啊雨水啊沖刷地布滿窟窿眼,那種殘酷、斑駁、創傷和自己內心的對位一下子感覺到看到了自己的身影,那種生命的同感形成了一種扭曲的、變態的美,而這種美恰好是中國人始終拿出來作為一種模式存在的。
梁克剛:這就是中國造型藝術有一種心理的要素,不是通過視覺因素來解決,他并不畫看到的,他畫的實際是心里想的或者感覺的東西。為什么我們說中國的繪畫,包括中國的雕塑,不是寫實的,不是仿真的,實際上是帶有一種主觀修改的,主觀的想象,或者對造型有一種期待。中國人看的松樹畫的是松樹,但表達的是一種人格,梅蘭竹菊,實際上最后表達的是人格和生命體驗,但最后體現出來的是一種視覺形象,不像西方研究光線,研究光線在自然中透射出來的反映,西方的繪畫是用視覺來控制的,用視覺的標準來解決的,但中國古典繪畫特別是繪畫體系,完全是心理性的創作,其實就是觀念性的創作,我認為中國很早就已經進入了一種觀念性的創作,只是說因為西方的現代主義運動開始之后,變成一種主觀的感受性的表達,從印象派開始有了這樣一個路徑,中國人其實早就解決了這個問題,只是我們片面地把傳統扔掉,拼命地向西方學習,這是一個誤區,因為鴉片戰爭后失去了文化自信,我們認為那個傳統可以讓我們更加強大。實際上,就這個問題我跟北大的朱青生老師有過一個交流,我認為他的談法對我有很大的啟發,他說并不是西方的傳統打敗了我們的傳統,而是西方的現代打敗了我們的傳統,是我們自己沒有更新,那么西方的現代先打敗了自己的傳統,然后再打敗我們的傳統。滿清之后,包括民國五四知識分子有一個誤區,這個誤區就是認為我們的傳統不如西方的傳統,所以我們要砸爛孔家店,把我們自己的傳統全部封存起來,讓它休眠,進行徹底的文化改造,這樣才可能帶來復興,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誤區,這個誤區就造成了一百多年來傳統的破壞和對傳統的擱置,所以我們的傳統實際上是停止了,它放在那里睡覺了,休眠了;而西方在那個傳統不斷地延伸、變化,它是一個活體,而且它的根脈沒有斷裂,而且我們學習最終解決不了我們的問題,文化本身的差異,世界觀、文化、生活習俗、倫理、生活習俗、社會的結構,這一切都有著巨大的差異,我們只是學一個樣式,肯定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邵譯農:其實在今天,經過中國這樣一百年的歷史,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和整個中國的文化精英目前的走向唯物質論、商業論,實際上是在西方的價值觀底下的一種追求,這進入了一種非常極端的狀態,在這種狀態底下,當代藝術整個也是在這個脈絡里頭,“無常之常”的走向實際上是一種回歸的狀態,也就是說把真正自己的價值重新能夠回家,回歸的這條路其實在今天是非常有價值和意義的,回到民族的自信上來,回到那種淡薄的狀態中來,回到自足的精神狀態中來,強調的是一種自我的生命的體驗,從新來梳理已經形成的這種混亂,這種混亂從價值觀上導致整個人的今天社會的種種原因,這種回歸對于藝術本體來說是回到這個整個對于藝術的一種從新認識,這個認識當代藝術的中國化的進程里頭,“無常之常”正處于這樣一個進程之中,因為一個外來的東西在其他國土上真正扎下跟來其實需要一個漫長的歷程,這樣一個歷程慢慢將元素溶解在這里頭,然后吸收這里的養分,得到修養之后生長出來的新的成果,這對于整個社會的心態的改變是非常有意義的。
梁克剛:確實是,也并不是只有我們幾個人這樣想問題,其實今天這一代知識分子、藝術家甚至包括政治家應該共同考慮的一種大的問題,只是我們在視覺藝術這個領域里面走了這一步,拿到國際上進行一種了碰撞,而且現在的反饋現在看起來工作是有價值的、有意義的、有效的,對方產生了反映,平等對話的一種需求,中國面臨著很大的機遇,無論是在體制層面、文化層面還是社會生活層面,都應該我們有一些自己的主張和方式,基于我們的文化傳統的有價值的轉換到方式,而不是簡單的拷貝的模式,我認為這是一個普遍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有可能我們也有可能給人類貢獻一些新的方法或者新的實驗的成果,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現在做的只是在當代藝術里面去實驗了一下這個過程,最開始的時候我沒有把它看做一個簡單的展覽,我覺得這是文化的一種愿望,一種嘗試,在這個領域里面。因為展覽畢竟要依托作品,我們要用作品說話,所以我很在乎的就是作品的創作,所以我很用心的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去尋找同類的藝術家,就是有這種共識的、作品能達到這種水準、有著清晰的理念,這種類型的藝術家,我們彼此交流比較多,而且大家也都在幫忙去尋找這樣一個藝術家,因為一兩個藝術家是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的,而且沒有好的作品也說明不了問題,最后出國展覽的感受就是如果沒有拿出很硬的作品擺在那里,你是沒有辦法把話說得讓人家信服的,所以我覺得這兩年出國辦展覽的人很多,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好的理念,沒有好的作品和構想的話,出去等于是打水漂,等于是沒有價值的。我們作為一種民間的力量,還是有一些文化上的愿景。所以我想張帆現在這個作品,從中國的文人畫和書法這樣的角度,進行了一種轉換,作品在展廳里的效果你也看到了,我認為歐洲人到展廳之后看到你的作品之后非常觸動,他知道這是當代的作品,他也知道這是抽象作品,但是他也知道這是中國人畫的,這個很有意思,這是很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因為中國有很多畫抽象畫的,如果我們不看標簽就不會意識到他是一個中國人的作品,你這種工作的嘗試有一種建構的特性。
張帆:我就是一直到零六年,你越畫覺得自己越虛無,那種狀態我相信很多做抽象藝術的人都會有,就是你特別依賴一個形式,必須要有一個形式,因為你形象沒有了,所以必須要有一個形式,形式實際上是自己挖了一個坑,把自己給埋了,很多特別大師的偉大的抽象藝術家,其實最終都會面臨這樣一個困局,最后已經完全拖離不了形式了,離開了之后畫的對象找不到了,比如最著名的波洛克,他想畫別的,但是他畫不出來,所以才借酒消愁。當時我就覺得一定要把表面形式拋棄掉,拋棄掉之后這個東西恰好慢慢就出來了,就是氣息或者氣味,這個畫就彌漫著一種可以聞得到,但不是某種具體的形象的東西,從這個點上來跟中國古典的繪畫或者書法來融合的話,這是一個比較高級的狀態。如果我們說是用古典符號的話,那跟用政治符號沒有什么區別。我不覺得藝術史上只有政治符號沒有感情,只有社會學關系,就被大家所記住或者怎么的。其實每一個留下名字的人都是有個人的情感在里面,絕不僅僅是一個符號而被記住,這種氣息有了之后,我覺得就是一個對傳統的學習的,或者一個再創造,因為你用的是油畫語言,但是氣味是中國的;另外一個,我覺得是古典藝術跟當代藝術有一個特別大的區別是,所有的古典藝術都需要修煉,我一直非常崇拜或者尊敬音樂家,是因為我覺得音樂家里面是欺騙性最小的,他必須在技術上修煉過關,除非你是一個天才,但天才只有莫扎特這樣的人,所以在視覺中這種欺騙性是非常大,古典藝術修煉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自我的證明,這點我覺得很重要,包括書法大家都寫同樣的字,寫同樣的話,同一個漢字,那你的書法作品拋棄基本功,實際上也是一種修煉。我覺得對于每個人來說,每個藝術家關注傳統的原因不一樣,但我個人是從這個角度來關注傳統,而且這個東西是一個手段,不是最終目的,它是一個階段性的東西,過了這個階段可能就會發生變化了,但是學習的過程和你對藝術比較深層次的領悟會一直留住的。
邵譯農:書法其實是很有意思的,書法按理說是一種非常模式化的東西,人人都照著這個東西寫,但是寫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進駐到一個層次的時候,實際上是進駐到每個人的心性里頭,也就是說心智的不同、人生體驗的不同、性情的氣度不一樣,那種生命的體驗出來的氣息是不一樣的,每個人筆畫之間的微妙的差異,就使得字的整個形態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那種可識別性并不是說語言形式本身,而是在氣的輾轉中力的分寸的拿捏和把握,導致的韻味和品格的差異是非常大的,中國文化里實際上師打開一個心域的,這個心域一旦打開之后在心界里產生一種東西,人的最重要的差距并不是在物質本身,而是在內心世界的內部的東西的區別,這個東西天壤之別,所以中國文化直接進入到人心界里頭。我覺得作為藝術家來操控藝術的時候,中國人并不擅長語言學的推進,從一種形式推進到就像機器的齒輪的咬合一樣,一個一暑假完成了卡尺的格子,中國的藝術家在語言的創造上并不是很強,他反而有的時候是一種感覺,物體放在那兒他內心世界產生的對物質所對應的虛空的內心世界的反映,然后把這個世界的表達借物來完成,完成的時候差別會非常大,所以我覺得中國文化的這種差別就把當代藝術的那種不可替代性,從形式和語言的差別轉變為內心體驗和生命體驗的差別上,這個差別是非常大的。
梁克剛:談到這個其實又談到那個根源了,也就是說為什么中國的藝術是這樣一種在很小的范疇里頭找這樣一個空間,從內心找空間而不是從外在的世界找空間,實際上根上還是哲學的世界觀,因為它是克制欲望的,整個西方的系統是張揚欲望的,包括西方的現代化社會,消費化,它是在鼓勵欲望,它前進的動力是欲望的開發,但東方恰恰是反著來的,包括整個儒家的系統,它實際上是在克制欲望,克己復禮,內心有一個更大的世界,所以書法在很小的尺度里面找一種趣味和自由,而且那種自由是在那么小的范疇里面無限,就像張帆說的,一萬個人寫一萬個字,都會不一樣,有的好到極致,有的差到極點,說到根上,整個中國文化就是這樣一個價值系統,這樣一個價值系統就是它的世界觀以及面對世界的方法有關系,包括道教佛教兩大宗教,包括儒家的這種雖然不算是宗教算是一種行為規范,都是要讓你克制欲望,都是讓你在內心世界和精神領域里開發更大的空間,這個自由是向內走的,而不是向外走的。
張帆:所以我們不能百分之百的就是中國傳統復古,它是有好的地方,但是也有特別大的局限,沒有科學的推進,沒有邏輯,它用一種方法在玩弄。
邵譯農:所以現在強調的應該是對東西方文化的整個的通吃。
梁克剛:有時候有一種感受我把它形象的說一下就是,傳統文化已經成為廢墟了,但是里面還有火種,沒有滅掉的火種,我們并不要把殘破的磚瓦搬回來,這個已經沒有意義了,而是應該把這個火種找到,像薪火傳遞一樣重新傳承,讓它在新的世界里面。
張帆:它有特別值得利用的東西,但這種利用價值不是世俗意義上的。
邵譯農:這里頭有一個問題是需要討論的,就是說西方人一直以來所走的方向是打開欲望的方向,而中國人一直走的是一條把欲望整個收斂起來的路線,著兩條路線都可以達到極高的境界,西方的欲望也不是今天的,從古羅馬開始一直延續的,精神上物質上有壓抑的時候,但很多時候是放開的,也就是時候在他們那個民族里達到一種欲望的絕對自由,然后讓你不斷地滿足于物質享受,但是這是在人的比較下層,他們的上層是滿足欲望以后達到的升華,進入到從實至虛的境界,他們是能夠產生這樣一個過程的,跟我們的至圣之路是一樣的,中國的至圣之路是要求你克制,然后修心養性,然后對物質的內心的排斥和放空,自然的人性的上升,把人性品格里最崇高的東西上升出來,這條路一直以來是中國文人所行的路線,但是現在中國的物質半開不開,中國人物質什么時候達到像西方人那樣滿足,而且還能上升,那我覺得今天的物質是根本達不到,也沒有那種可能,因為中國人太貧窮,尤其是內心里的貧窮,幾百年以后能不能達到西方人那樣欲望滿足之后的升華,這個仍然是看不到希望的。
梁克剛:我覺得現在中國的問題恰恰是走了西方的方式,把欲望打開了,然后不斷地去尋求現實的滿足,但是現在的地球承受不了這個的,實際上地球誒有能力養這么多人,讓這么多人以這樣的形式生活。歐洲人意識到這個問題了,他們在往回走,我們正在往那個地方去,但是中國人是沒有辦法到那個終點的,因為走到那個終點地球基本上要崩潰了,根本承受不了這樣一種索取,所以我認為現在這種調整應該就是說在中國這種真正的社會、生活、文化各個方面從新開始反思,我們怎么去解決這個矛盾,是不是還應該繼續這樣走向去,我們現在已經在消費全世界一半的石油了,多嚇人啊,這還不是所有的人都買上汽車了。
邵譯農:因為物質的路線,就像從長江上順江而下一樣,你只要放開欲望就順江直接下去了,中國的至圣之路是逆江而上,直接去尋找這個本源的,那么這兩條路實際上是差開很遠的,所以中國文化之所以有制高點一直是在尋找本真和本源的一條路,這就是世界的虛空的部分,始終是精英部分必須恪守的部分,西方走的是實的部分,我覺得實和虛兩個時空的并置才會完美。
梁克剛:當然我們考慮的問題非常多,但我們需要行動去表達這樣的愿望和訴求。作為藝術界的人士和方法,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在文化上引發一種關注和討論,引發東西方的碰撞,西方人也會看到這個展覽,也會反思他們的藝術會有什么問題,中國人看到了以后會思考我們還有什么新的可能性,我們不需要全盤的向西方學習,而是自己能拿出一些新的解決方案,拿出一種新的理念和新的貢獻。今天時間也有限,可能最后話題還得繞回來,雖然現在我們還未達到這個目標,目前我們還在推進這個展覽,要在國外繼續走下去,我們也是想通過藝術展覽把我們包括今天討論的和平時溝通的思考的很多東西附加到展覽中去,產生一些碰撞。我想可能主要是這樣一個愿景,我們當然是希望越走越好,現在也給了我們一個很大的信心和支撐,剛剛開始出去的時候還是感覺惴惴不安,害怕達不到國際一線的藝術標準,現在看起來走出去的感覺包括反饋給我們的信息,也確實給了我們一個很大的信心,我們完全有能力在全世界做非常好的受尊敬的展覽,我們也有能力輸出一種新的藝術樣式和新的藝術理念,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大的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