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高興今天在這里談論我的題目。我將結合最近的實踐回顧進行分享,而不是僅僅進行理論評述。在這分享中,我會質疑一些科學家預測的,人類歷史將終結于“奇點”這個說法的思考路徑,并嘗試著給出討論。“奇點”絕對是個合理的預測,尤其當這個星球上最強大的計算機——人類大腦給出這個“運算結果”的時候。然而,到底是輸入了怎樣的代碼,人們會得到這個答案?我們(大約只存在了40余萬年的智人)有沒有可能提出除了“奇點”之外的任何答案呢?
在《銀河系漫游指南》第一卷中,有一個關于一群聰明的老鼠的故事給了我很多啟發。為了找到宇宙的終極答案,老鼠們建造了一臺名為“深度思考(Deep Thought)”的機器。這是一臺超級計算機,經過了750萬年的計算,終于得出了一個準確的答案:42。不過“深度思考”只知道答案,這個答案的意義需要另一臺更強大的計算機——“地球”才能做到。但不幸的是,就在答案出來的前五分鐘,地球被強制摧毀,因為它阻礙了一條“賽博空間高速公路”的建設。
這個故事可謂是發生在我們星球上的“強拆”事件的宇宙版本。這讓我不禁聯想人類會不會也因為某些像“阻礙賽博空間高速公路上的建設”的原因而滅絕。如果真的發生了這種情況,那么像后人類、宇宙技術、行星計算和星際遷移等等世界技術圖景的哲學討論可能就是智人臨終前的最后一個夢。我想,當我們詢問自己制造出的“超級計算機”:“人類歷史的終結是什么?”的時候,這就是科幻小說的魅力,它提供了輸入的代碼,而輸出的卻不僅是“奇點”。
這里我想介紹一下科幻小說家娥蘇拉(Ursula KroeberLe Guin)為她的讀者提供的方案。她說:“我并非提議回歸石器時代。我的目的既非反動,甚至也不算保守,而是單純的顛覆。烏托邦式的想像似乎被困住了,與資本主義、工業主義和人類群體一樣,都走上只關心未來發展的單行道。我一心想做的,不過是設法把小豬放回小路上。”

Ursula KroeberLe Guin的部分作品
娥蘇拉以孩童式的想象力和對于資本主義社會與政治的深刻洞察來建構故事而聞名。她將科幻小說從線性歷史,一種工業革命以來的時間觀點解放出來,也將智人從單一同質的生物特性中解放出來。奇點的確是一種工業時間,線性的,班雅明所謂的“非彌賽亞時間”的結果。
眾所周知,“技術奇點”表明人類正在接近一個事件點,在這個點上現有的技術可能被完全拋棄,或者人類文明可能被徹底顛覆。這一點之后是像黑洞一樣完全不可預測的事件世界(evnet horizon)。曾與圖靈合作的數學家Irving John Good在1965年提出,技術奇點(他稱之為“智能爆炸”)的必要條件是人類中心主義的消亡。而剩下的有待發明的超級智能機器應該是人類需要完成的最后一項發明。要實現智能爆炸,首先需要人工智能的進步,其次是增強智能(augmented intelligence);前者使機器迭代,而后者創造超人,或者說,超人類。
有關奇點的推論都來自線性發展的預設。除了娥蘇拉,另一位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Philip Kindred Dick)還提供了輸入我們“超級計算機”的一些其他方案。迪克的作品(可能也包括他自己)以混合時空、現實和幻像交疊以及分裂的角色身份而聞名。例如,《龍比克》(UBIK)這本小說中,無處不在的噴霧劑可以解決宇宙的所有神秘難題,包括扭曲時間和空間、打破生與死的邊界以及記憶和身份之間的沖突。此噴劑作為地球上和宇宙中一切事物的解毒劑,卻不知發源于何處。而在《高堡奇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這部作品中,一種新的另類歷史被創造出來。迪克問,如果德日同盟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今天的世界會是什么樣子?在Dick的故事中,“奇點”就是多元(plurality)。在一部紀錄片的訪問中,他曾說過:
“作為一個程序員,我們向他呼喊上帝時,編程的結果將顯然將我們納于時間之內,而他非在他們之中。我們生活在一種被設定與計算的現實里。我們唯一的線索就是當某個變量發生變化時,現實跟著發生了一些變化。”
——The Worlds of Phillip K Dick. 2015
由此,他一生的作品提示了一個共同的觀點:只有當我們看到社會運行中的裂縫時,我們才會察覺到世界一成不變的法則是被籌劃出來的。這也是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在他一篇關于迪克的紀念文章中寫道的,“迪克總是在渲染歷史(render history)。”
科幻小說通常被理解為試圖想象不可想象的未來。但它最深刻的主題實際上蘊含在我們的歷史現在(historical present)。迪克小說的未來是通過將我們的當下渲染成幻想未來的過去而使其成為歷史,,就像他書中最激動人心的情節一樣。“
——Fredric Jameson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p345
對我來說,渲染歷史是對技術奇點到來的反抗。這與許多科幻小說中通常隱含的場景背道而馳:世界末日,極權統治、階級區分、高科技低等生活,等待英雄救贖等。詹明信繼續說:
“想想迪克創造歷史的能力吧。消費社會、“媒體奇觀”的社會,晚期資本主義——不管人們怎么稱呼——令人震驚的是,它失去了對歷史維度中過去和未來的感知。這是對歷史差異想象力的匱乏——馬爾庫塞稱之為烏托邦馳騁的畏縮——是一種更顯著的晚期資本主義病理癥狀,較“自戀”狀況尤甚。”
—出處同上
也許奇點離我們并沒有那么近,因為顯然對人類來說發明一臺比我們自己更聰明的機器是困難的。或者,如果我們能成功地讓機器閱讀《圣經》和《資本主義》,“它們”可能比我們自己能更好地拯救這個星球的文明。或者我們也可以想象,人機界面最終不會是一個可視化的擴展現實(AR),而是一個想象中的腦機一體裝置。它能讓我們變成Motoko Kusanagi(草薙素?)少佐,在攻殼機動隊(Ghost in the Shell )作品里描繪的新物種那樣,我們的意識與網絡集體意識合一,棲息于無限的網絡中,不再擔憂人類文明的覆滅,或人類中心主義者對于不可預測世界的恐慌。
我們應該注意到,在某種程度上,世界主義本身也是一個“奇點”。一方面,它來自人類中心論、技術引起的世界同質化、媚俗的啟示錄、個人主義的賽博朋克英雄以及救贖犧牲的受害者; 另一方面,它來自于星際主義者的分裂想像,尤其是在硬科技類科幻小說傳統中,如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中那樣,宇宙成為無差別的黑森林,遵從了生物(其實只是智人)本性沖動。如果說我們從娥蘇拉和迪克身上學到了什么,那就是: 除非你同時接受過去和未來,否則你將無法擁有現在。過去和未來,未來和過去。因為他們都是真實的,只有現實被承認的時候,此刻才是真實的。如果人們不理解希望,那么又如何能理解現實呢?
歷史的液態化是對抗奇點和進化觀歷史的實踐,必然也是一種理論實踐。用日本帳篷戲劇導演櫻井大造(Daizo Sakurai)的話說,這是一個“反思的場”,它將當下的現實(事實上,它僅僅是一個現實驅動的維度)變成“虛構”。那么,我們如何利用這個場來理解現實?它必須是少數幾個同時存在著他者和諸眾的場,當互聯網給我們“希望”時,我們又應該如何理解基于此的現實?
今年4月,我策劃了一個名為”鄉建中國思想展“ (Plot the Soil: Reconstructing the Country of China )的展覽。展覽在杭州蕭山區靠近湘湖的高帆攝影藝術館暨高帆紀念館舉行。蕭山是中國第一次農民運動的地方。那時抗議者們抵制重稅盤剝,要求東家減租。湘湖后來也成為陶行知和曉莊師范的遺產所系之處,以湘湖師范學校的名字重新辦學。如果你再看看現在的蕭山和湘湖,就會明白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鄉村教育的思想者們播種的種子是如何發芽結果。事實上,當你走在當代中國鄉間的時候,你會意識到有許多不同的思想與實踐形態疊加其上。鄉建思想史就也是空間的歷史。
在這次展覽中,我們的研究人員對重慶北碚進行了案例研究。在這個生動的案例中,盧作孚先生的私人船運公司運送了超過10萬人的難民以及大批的物資,來為大后方支持對日作戰。20世紀30年代,許多像中國鄉建的關鍵性人物比如梁漱溟、陶行知、晏陽初等都把他們的教育機構搬到了北碚。同時,中國作家老舍還在這里完成了他最著名的小說《四世同堂》。

重慶北碚的歷史舊照
現在的北碚,你仍然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建筑,它們如何造就了中國的第一座現代化城市。這座城市有中國第一座城市公園——北碚溫泉公園,第一座公共教育中心,第一個西方意義上的“圖書館”。所有的這些建筑是由丹麥建筑師守爾慈(Jesper J. Schultz)設計。他應盧作孚的邀請,在規劃一個全新的城市理念指導之下展開設計工作。
面對這么多的史料,我在考慮將過去和當下聯結起來。作為當代歷史的一個分支,如何使北碚變成一個融合過去和未來的空間呢?隨后,我與MetaDAO(幻境小組)合作,利用去中心化的網絡平臺Decentraland一比一還原了北碚的市中(https://play.decentraland.org/?island=Icuvo&position=126%2C-52&realm=fenrir),一個基于區塊鏈技術的元宇宙。你可以在線上穿越20世紀30年代北碚的大街小巷。
在盧作孚的規劃中,作為現代化的城市,北碚應當培育一種現代化的市民文化生活,尤其是“公共生活”。在當時,丹麥建筑師改變了大多數北碚傳統建筑的長屋檐,取而代之的是斯堪的納維亞風情的短檐。我覺得陽光在丹麥比在重慶更受歡迎,因為重慶人經常暴露在陽光下。總之,北碚的建筑看起來一點兒也不“中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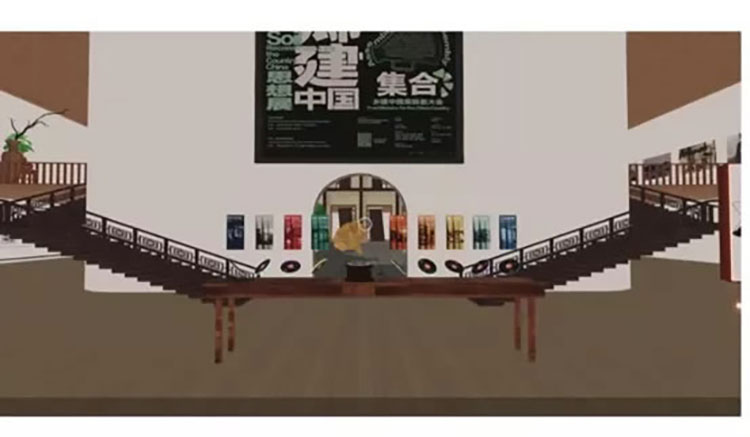
鄉建中國北碚項目的部分效果呈現

鄉建中國北碚項目的詳細信息
除了代表性的建筑,我們還基于Decentraland在北碚設置了一個DJ電臺,人們可以在這里聽到當代北碚市民的采訪錄音。元宇宙是一種創新,在這里我們可以保存和定格歷史——不但有建筑空間的回憶,還有關于現在和過去的聲音和影像記憶。在我們的虛擬北碚中,人們還可以站在(字面意義上的)汽車或飛機上面,鳥瞰整個小鎮。這非常有意思,因為即便你親自到了那里,也很難有這樣的體驗。
我相信這就是“網絡”的力量,以電力為基礎,創造了一種嶄新的有關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敘事。一種分叉的歷史,一種歷史的”第二人生”。一種將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他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書中稱為“底層政治”(infrapolitics)的東西給呈現出來,亦即將底層政治形象化成可見光譜。就像福柯在他著名的,也值得我們再多花些精力關注的短篇作品”無名人的生活”(Lives of Infamous man) 里說的那樣,歷史總在權力之光照射處:
……當與權力接觸時刻,一束光才能照到那些幽暗本來該隱藏的巨大的生命群體。…這些仿佛根本不存在過的生命,只是因為和權力相撞擊才有機會幸存下來,而這個權力本來只希望消除他們,或者至少抹消他們的痕跡,正是許多偶然的際遇混合在一起,才使得這些生命能夠在我們這里重現。
— Michale Foucault,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ume 3: Power, Lives of Infamous man. p157-175
要有另一束光,從外頭照亮那瞬間,諸眾或底層/弱勢的歷史才能顯現。而我們可以讓Decentraland,這個科技樂觀主義的區塊鏈商業地主游戲變成歷史的第二人生,使得底層、他者、諸眾之貌的呈現得以可能。這個項目的許多參與者都是志愿者。我們可以將科幻小說變成“現實”,我們可以將已經發生故事說給未來聽,從而聯結過去和將來,而不僅是由現實驅動的一種不得不的當下。只有這樣,即便我們知道“奇點”是最終的答案,至少我們了解理由,也知道我們付出過實實在在的努力。

中國美術學院跨媒體跨媒體藝術學院網絡社會研究所部分作品呈現
(以上講稿由董辛欣翻譯,已經由分享者本人確認并授權發表。)

黃孫權 Sunquan Huang
黃孫權,學者、策展人、藝術家、工學博士。現為中國美術學院教授,跨媒體藝術學院網絡社會研究所所長,視覺中國協同中心鄉土實踐與空間生產研究方向導師。在中國美術學院網絡社會研究所的所長職位上,已經舉辦過五屆國際網絡社會年會,建立了70位國際知名學者與百位青年學者的研究型網絡,包含了以太創訪人Vitalik、微軟社會策略發展的CTO以及《基進市場》作者之一的Glen、以及以及英、美、日、歐等重要機構的領導者。舉辦多場文藝黑客松(art hackatton),參與者超過400位藝術家、策展人、設計師、程序員。建立分布式網絡平臺的社交媒體平臺實踐(social.caa-ins.org),并與metaDao共同在Decentralland上打造了1940年代北碚城市的模型,將100年來的中國鄉建思想搬到元宇宙上。逐漸打造出中國獨特的文化—技術的新生力量網絡。